
- 2019年7月10日-12日,上海攬境展覽主辦的2019年藍(lán)鯨國(guó)際標(biāo)簽展、包裝展...[詳情]
2019年藍(lán)鯨標(biāo)簽展_藍(lán)鯨軟包裝展_藍(lán)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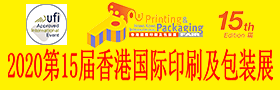
- 今日排行
- 本周排行
- 本月排行
- 膠印油墨
- 膠印材料
- 絲印材料
???????????????
2013-03-05 09:20 來(lái)源:FT??? 責(zé)編:??
- 摘要:
- ???????????(New York Public Library)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【CPP114】訊:幾年前,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(New York Public Library)的理事們做出了一個(gè)勇敢的決定,該館的建筑需要升級(jí)。于是他們邀請(qǐng)著名英國(guó)建筑師諾曼•福斯特(Norman Foster)為這座曼哈頓的標(biāo)志性大樓設(shè)計(jì)21世紀(jì)風(fēng)格的內(nèi)部裝飾,同時(shí)兼具實(shí)用、前衛(wèi)以及節(jié)約成本等特點(diǎn)。
.jpg)
去年年底,這一預(yù)算高達(dá)3億美元、并且還在追加當(dāng)中的裝修方案終于出爐,并引發(fā)了激烈爭(zhēng)論。先不談福斯特關(guān)于移除某些色調(diào)偏暗的19世紀(jì)風(fēng)格裝飾,以打造明亮通透效果的提議。真正引發(fā)爭(zhēng)議的是他希望把很少有人翻閱的老舊圖書(shū)從地上展區(qū)移走,并放入地下儲(chǔ)藏。此舉可以使圖書(shū)館有條件展出來(lái)自紐約其他地方的流行藏品(并出售其他大樓),以及開(kāi)設(shè)一家咖啡廳。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館長(zhǎng)安東尼•馬克斯(Anthony Marx)解釋道:“我們想把地上區(qū)域給人使用,而不是用來(lái)儲(chǔ)藏圖書(shū)。”或如福斯特所言:“這是一個(gè)為紐約人打造一處重要公共空間的機(jī)會(huì)。”該方案讓某些紐約名流驚恐不已。一位著名的紐約慈善家問(wèn)道:“我們真的想在那里開(kāi)設(shè)一家星巴克(Starbucks),而不是存放圖書(shū)嗎?”《紐約時(shí)報(bào)》(New York Times)的著名建筑評(píng)論家邁克爾•基梅爾曼(Michael Kimmelman)近期對(duì)有“名人設(shè)計(jì)師”之稱(chēng)的福斯特發(fā)起了猛烈攻擊,稱(chēng)他的方案是“狹隘平庸的臺(tái)階大雜燴……可能成為工程領(lǐng)域的阿拉莫(Alamo)之戰(zhàn)……以及一個(gè)金錢(qián)陷阱”。
但事實(shí)上,受這一方案影響的遠(yuǎn)不僅是建筑品味。馬克斯等人正在努力回答的關(guān)鍵問(wèn)題是:如今公共圖書(shū)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么?為什么還會(huì)有人確實(shí)需要這些實(shí)體書(shū)庫(kù),不論它們是放置在由福斯特設(shè)計(jì)的位于曼哈頓的通透大樓中、地下儲(chǔ)藏室里、或是其他任何地方?
這是一個(gè)非常難以回答的問(wèn)題。當(dāng)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靠吸收多家小型私人圖書(shū)館的藏書(shū)于1895年最初建立時(shí),其創(chuàng)建理由非常顯而易見(jiàn)。圖書(shū)是提供知識(shí)以及娛樂(lè)的寶貴載體,學(xué)者(或窮人)很難獲得圖書(shū)。
因此,按照典型的美國(guó)風(fēng)格,慈善家們登上舞臺(tái)為作為公共品的圖書(shū)館提供支持,并留下讓他們引以為傲的遺產(chǎn)。薩繆爾•J•蒂爾登(Samuel J. Tilden)以及約翰•雅各布•阿斯特(John Jacob Astor)等名流為紐約的圖書(shū)館捐贈(zèng)了大筆資金。1901年安德魯•卡內(nèi)基(Andrew Carnegie)捐獻(xiàn)了520萬(wàn)美元,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單筆捐贈(zèng)之一。這種傳統(tǒng)延續(xù)到了現(xiàn)在:2008年,私募股權(quán)大亨史蒂芬•施瓦茨曼(Stephen Schwarzman)捐贈(zèng)了1000萬(wàn)美元,用于修葺42號(hào)大街上最具標(biāo)志性的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大樓。此舉使他的名字和這座大樓永遠(yuǎn)連在了一起,并被鐫刻在大樓廊柱的底座上(某些紐約人認(rèn)為這一榮譽(yù)的售價(jià)太低)。
雖然像施瓦茨曼這樣的人或許會(huì)關(guān)心柱上留名,但當(dāng)代公民是否確實(shí)關(guān)心這些實(shí)體書(shū)籍則不甚明了。近年來(lái)西方世界的圖書(shū)館訪(fǎng)問(wèn)量以及圖書(shū)發(fā)行量持續(xù)下滑,因?yàn)樵絹?lái)越多的人轉(zhuǎn)向了電子書(shū)、維基百科(Wikipedia)和谷歌(Google)。為對(duì)抗這一趨勢(shì),圖書(shū)館紛紛開(kāi)始安裝新系統(tǒng),可以提供電子圖書(shū)借閱、在線(xiàn)閱讀出版物以及用郵寄方式將圖書(shū)送到借閱人手中等服務(wù)。其中某些嘗試正變得越來(lái)越大膽——甚至可以說(shuō)得上是絕望。例如,本月德克薩斯州某縣決定成立一家為自身社區(qū)服務(wù)的新圖書(shū)館,但服務(wù)范圍僅限于線(xiàn)上,沒(méi)有任何配套的實(shí)體圖書(shū)或者建筑。
這讓很多學(xué)者、出版商和圖書(shū)管理員都感到頗為恐慌。他們指出,電子書(shū)畢竟是不是永久性的;相比之下,實(shí)體書(shū)籍則具有歷史價(jià)值。
單是訪(fǎng)問(wèn)圖書(shū)館的這一行為本身就能讓人產(chǎn)生一種群體歸屬感。或者正如馬克斯所言:“在洞穴中與電腦為伴的孤單生活并不適合我們;我們需要走出門(mén)來(lái)與人交流。”
但馬克斯也明白,變革的壓力正在日漸增大。而他所在的機(jī)構(gòu)恰巧是訪(fǎng)問(wèn)人次不降反升的少數(shù)幾個(gè)西方圖書(shū)館之一。去年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的訪(fǎng)問(wèn)人次達(dá)到1820萬(wàn),較2010年增長(zhǎng)了3.4%。但吸引人們到來(lái)的原因并不一定是館藏書(shū)庫(kù)。
.jpg)
但事實(shí)上,受這一方案影響的遠(yuǎn)不僅是建筑品味。馬克斯等人正在努力回答的關(guān)鍵問(wèn)題是:如今公共圖書(shū)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么?為什么還會(huì)有人確實(shí)需要這些實(shí)體書(shū)庫(kù),不論它們是放置在由福斯特設(shè)計(jì)的位于曼哈頓的通透大樓中、地下儲(chǔ)藏室里、或是其他任何地方?
這是一個(gè)非常難以回答的問(wèn)題。當(dāng)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靠吸收多家小型私人圖書(shū)館的藏書(shū)于1895年最初建立時(shí),其創(chuàng)建理由非常顯而易見(jiàn)。圖書(shū)是提供知識(shí)以及娛樂(lè)的寶貴載體,學(xué)者(或窮人)很難獲得圖書(shū)。
因此,按照典型的美國(guó)風(fēng)格,慈善家們登上舞臺(tái)為作為公共品的圖書(shū)館提供支持,并留下讓他們引以為傲的遺產(chǎn)。薩繆爾•J•蒂爾登(Samuel J. Tilden)以及約翰•雅各布•阿斯特(John Jacob Astor)等名流為紐約的圖書(shū)館捐贈(zèng)了大筆資金。1901年安德魯•卡內(nèi)基(Andrew Carnegie)捐獻(xiàn)了520萬(wàn)美元,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單筆捐贈(zèng)之一。這種傳統(tǒng)延續(xù)到了現(xiàn)在:2008年,私募股權(quán)大亨史蒂芬•施瓦茨曼(Stephen Schwarzman)捐贈(zèng)了1000萬(wàn)美元,用于修葺42號(hào)大街上最具標(biāo)志性的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大樓。此舉使他的名字和這座大樓永遠(yuǎn)連在了一起,并被鐫刻在大樓廊柱的底座上(某些紐約人認(rèn)為這一榮譽(yù)的售價(jià)太低)。
雖然像施瓦茨曼這樣的人或許會(huì)關(guān)心柱上留名,但當(dāng)代公民是否確實(shí)關(guān)心這些實(shí)體書(shū)籍則不甚明了。近年來(lái)西方世界的圖書(shū)館訪(fǎng)問(wèn)量以及圖書(shū)發(fā)行量持續(xù)下滑,因?yàn)樵絹?lái)越多的人轉(zhuǎn)向了電子書(shū)、維基百科(Wikipedia)和谷歌(Google)。為對(duì)抗這一趨勢(shì),圖書(shū)館紛紛開(kāi)始安裝新系統(tǒng),可以提供電子圖書(shū)借閱、在線(xiàn)閱讀出版物以及用郵寄方式將圖書(shū)送到借閱人手中等服務(wù)。其中某些嘗試正變得越來(lái)越大膽——甚至可以說(shuō)得上是絕望。例如,本月德克薩斯州某縣決定成立一家為自身社區(qū)服務(wù)的新圖書(shū)館,但服務(wù)范圍僅限于線(xiàn)上,沒(méi)有任何配套的實(shí)體圖書(shū)或者建筑。
這讓很多學(xué)者、出版商和圖書(shū)管理員都感到頗為恐慌。他們指出,電子書(shū)畢竟是不是永久性的;相比之下,實(shí)體書(shū)籍則具有歷史價(jià)值。
單是訪(fǎng)問(wèn)圖書(shū)館的這一行為本身就能讓人產(chǎn)生一種群體歸屬感。或者正如馬克斯所言:“在洞穴中與電腦為伴的孤單生活并不適合我們;我們需要走出門(mén)來(lái)與人交流。”
但馬克斯也明白,變革的壓力正在日漸增大。而他所在的機(jī)構(gòu)恰巧是訪(fǎng)問(wèn)人次不降反升的少數(shù)幾個(gè)西方圖書(shū)館之一。去年紐約公共圖書(shū)館的訪(fǎng)問(wèn)人次達(dá)到1820萬(wàn),較2010年增長(zhǎng)了3.4%。但吸引人們到來(lái)的原因并不一定是館藏書(shū)庫(kù)。
-
 相關(guān)新聞:
相關(guān)新聞: - ·書(shū)香中國(guó)成2013年中國(guó)圖書(shū)館年會(huì)主題 2013.03.01
- ·雅昌參展2013世界美食圖書(shū)展備受推崇 2013.02.26
- 關(guān)于我們|聯(lián)系方式|誠(chéng)聘英才|幫助中心|意見(jiàn)反饋|版權(quán)聲明|媒體秀|渠道代理
- 滬ICP備18018458號(hào)-3法律支持:上海市富蘭德林律師事務(wù)所
- Copyright © 2019上海印搜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(huà):1881662209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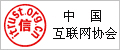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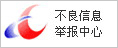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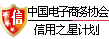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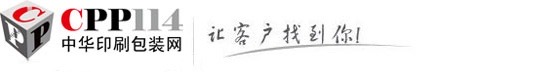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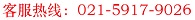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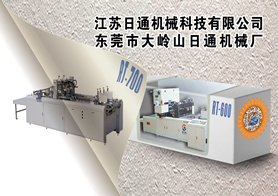








意商城news.jpg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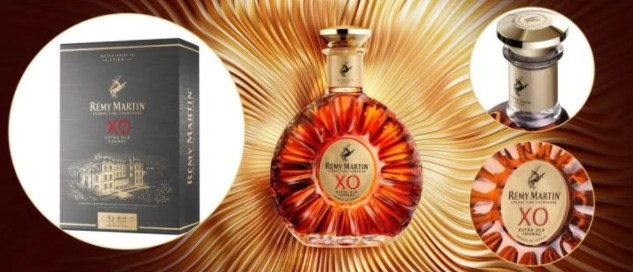

 主站蜘蛛池模板:
在线观看污视频网站
|
国产精无久久久久久久免费
|
精品九色
|
亚洲一区在线免费
|
少妇性按摩无码中文a片
|
久久国产免费观看精品3
|
一本一道波多野毛片中文在线
|
欧美不卡一区二区
|
日日摸人人看夜夜爱
|
国产在线播放线播放
|
少妇高潮呻吟A片免费看软件
|
久久久国产成人一区二区三区
|
欧美做受视频播放
|
青娱乐91在线
|
亚洲成在人线aⅴ免费毛片
久中文字幕
|
亚洲精品国产成人99久久6
|
亚洲国产成人AV片在线播放
|
永久免费的啪啪网站免费观看浪潮
|
国产97免费视频
|
国产精品麻豆自拍
|
狠狠婷婷综合久久久久久
|
看黄色特级片
|
国产干b视频
|
国产3级在线
|
人人妻人人澡人人爽人人dvd
|
性一交一乱一伦一色一情丿按摩
|
国产福利片无码区在线观看
|
久久久久久亚洲
|
国产在线激情
|
老熟女高潮喷了一地
|
亚洲精品乱码久久久久久蜜桃不爽
|
在线观看一区二区视频
|
高潮迭起av乳颜射后入
|
中出乱码av亚洲精品久久天堂
|
狠狠噜天天噜日日噜AV
|
51成人精品网站
|
久久午夜无码鲁丝片秋霞
|
久草在线公开视频
|
欧美三级视频
|
精品人妻无码一区二区三区蜜桃
|
被男狂揉吃奶胸高潮视频在线观看
|
主站蜘蛛池模板:
在线观看污视频网站
|
国产精无久久久久久久免费
|
精品九色
|
亚洲一区在线免费
|
少妇性按摩无码中文a片
|
久久国产免费观看精品3
|
一本一道波多野毛片中文在线
|
欧美不卡一区二区
|
日日摸人人看夜夜爱
|
国产在线播放线播放
|
少妇高潮呻吟A片免费看软件
|
久久久国产成人一区二区三区
|
欧美做受视频播放
|
青娱乐91在线
|
亚洲成在人线aⅴ免费毛片
久中文字幕
|
亚洲精品国产成人99久久6
|
亚洲国产成人AV片在线播放
|
永久免费的啪啪网站免费观看浪潮
|
国产97免费视频
|
国产精品麻豆自拍
|
狠狠婷婷综合久久久久久
|
看黄色特级片
|
国产干b视频
|
国产3级在线
|
人人妻人人澡人人爽人人dvd
|
性一交一乱一伦一色一情丿按摩
|
国产福利片无码区在线观看
|
久久久久久亚洲
|
国产在线激情
|
老熟女高潮喷了一地
|
亚洲精品乱码久久久久久蜜桃不爽
|
在线观看一区二区视频
|
高潮迭起av乳颜射后入
|
中出乱码av亚洲精品久久天堂
|
狠狠噜天天噜日日噜AV
|
51成人精品网站
|
久久午夜无码鲁丝片秋霞
|
久草在线公开视频
|
欧美三级视频
|
精品人妻无码一区二区三区蜜桃
|
被男狂揉吃奶胸高潮视频在线观看
|